2024-05-02
656次浏览 发布时间:2024-02-24 11:16:43 编辑: 中信书院

杨绛先生过世三年了。
三年前的那个5月,朋友圈铺天盖地的悼念文章涌来。一时间,好像人人知道她是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。每个人都在唏嘘:我们仨终于团聚了。
1
一提到杨绛,似乎永远撇不开她是钱锺书的妻子这个身份。人们怀念她,多少也是在缅怀钱杨二人之间一生相濡以沫的爱情。

好像要在这个难以相信爱情的年代,留下一点曾经有人真心相爱过的证据。
然而杨绛的一生,岂是一个“钱锺书的妻子”就能涵盖的呢!
尽管她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甘愿扮演一个最普通的妻子的角色,收敛光芒,默默地支持钱锺书的创作事业,但是,甘做“灶下婢”的杨绛,可不是真的只会以丈夫为中心、围着锅台打转的那种“贤妻”。
她的才华太过耀眼,即便是站在钱锺书这样久负盛名的大才子跟前也毫不逊色;她一生所获的赞誉和光环,也绝不是靠一个才华横溢的丈夫得来的。
尊称一声“先生”,她当得起。
2
没有钱锺书的时候,杨绛已经是杨绛。
读清华的时候,朱自清是她的老师,把她的作品推荐到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。
跟钱锺书结婚之后,说两人一起出国留学,人们都以为是杨绛跟着钱锺书出去的。其实呢,一开始是杨绛跟着钱锺书去牛津没错,但是钱锺书拿到学位之后,又跟着杨绛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了。
期间杨绛还生了一个女儿。

我们仨
回国后,钱锺书在清华做过教授,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过英文系主任。
相比之下,又要带孩子、又要照顾家庭的杨绛,履历上也没有一点落后——她做过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。抗战期间,苏州沦陷,她的母校振华女校搬到上海,她还曾义不容辞担任起校长的职务。
除此之外,虽然杨绛一直说她的主业是研究和译介外国文学,创作只是业余爱好,但就这个“业余爱好”而言,她出名也比钱锺书要早。
1942年,杨绛写了一个剧本叫《称心如意》,1943年在上海公演,一炮走红。此后,她又陆陆续续创作了《弄假成真》、《游戏人间》等剧作品,相继在上海公演。

《称心如意》某期剧照
虽然她不是专业剧作家,而且也算得上是新手,但是连著名的剧作家夏衍看了她的剧都说:“你们都捧钱锺书,我却要捧杨绛!”
而后来让钱锺书名声大噪的《围城》,那时候还没开始动笔。
3
论文学创作,钱锺书有《围城》,杨绛有《干校六记》、《洗澡》。丈夫去世之后,她又写了散文集《我们仨》,用读者的话说,这本书“不敢轻易看、看了就要掉眼泪”。

论主业做研究,钱锺书有传世之作《管锥篇》,杨绛的学术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——她搞外国文学研究,翻译过不少作品,早年就得到过翻译大家傅雷的赞赏,后来朱光潜也说,我们国家的散文小说翻译就属杨绛最好。
1978年,杨绛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出版。恰好那年西班牙国王携王后访华,杨绛应邀参加国宴。当时邓小平得知她从西语原文翻译了这本书,非常惊讶地问她是什么时候翻译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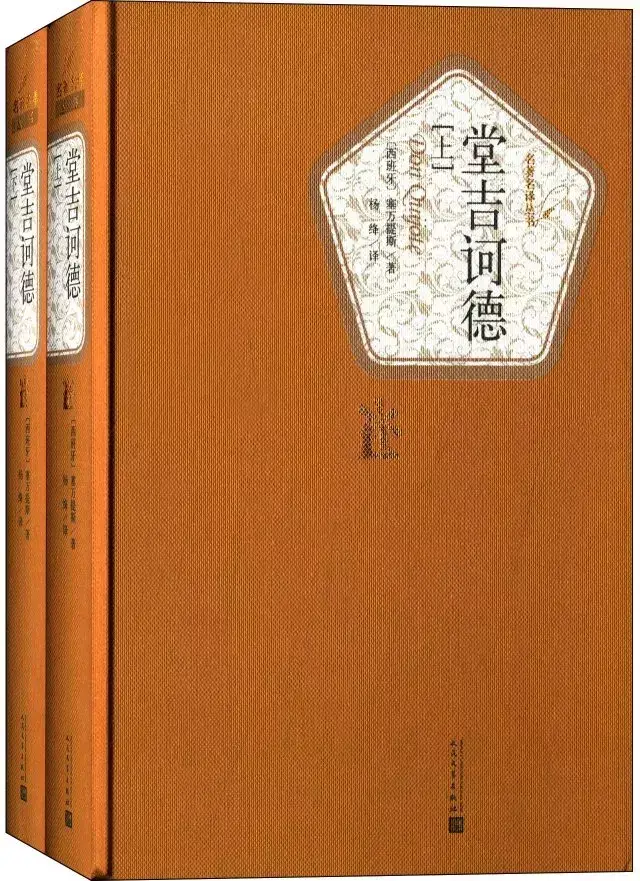
《堂吉诃德》 杨绛译本 1987版
毕竟,那之前的数年间,大环境极度恶劣,谁都没想到杨绛会在那期间默默地翻译出这么重量级的作品。她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,译稿“被没收、丢弃在废纸堆里”、“九死一生”,是历尽磨难才终于被保全下来。
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,杨绛之前并不会西班牙语,她是在47岁的时候才下定决心要自学西语的,而且是“偷空自学”!
那么这“偷空自学”的成果究竟怎样呢?
翻翻履历就知道,不仅有《堂吉诃德》这样的大部头译作,杨绛甚至还担任过清华大学西语系的教授!
4
正是因为是这样“最才的女”,所以她为家庭、为支持丈夫所牺牲的一切,显得格外珍贵。
杨绛曾经对钱锺书说过这样的话:“墨水洒了,我来洗。衣服破了,我来补。只要是你做不了的事情,我都可以学习去做好。”
钱锺书写作《围城》的期间,时值上海沦陷,工作没有着落,要靠岳父把自己的课时让出来给他赚点课时费贴补家用,每天只能写500个字。

为了这500个字,杨绛承担了里里外外几乎所有的家务。因为想节省开支,好让钱锺书省下一些讲课的时间来创作,她把家里的女佣都辞退了,连劈柴这样的事情都得自己亲手做。
更难得的是,她始终是钱锺书的“第一读者”,毫无保留地给予他一个完美读者的反馈。
“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,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。我笑,他也笑;我大笑,他也大笑。有时我放下稿子,和他相对大笑,因为笑的不是书上的事,还有书外的事。我不用说明笑什么,反正彼此心照不宣。”
有这样的妻子陪伴在侧,钱锺书虽然写了《围城》,却从来没有以为他自己的婚姻是一个围城;又或者,他在自己的这座围城中安坐,从不后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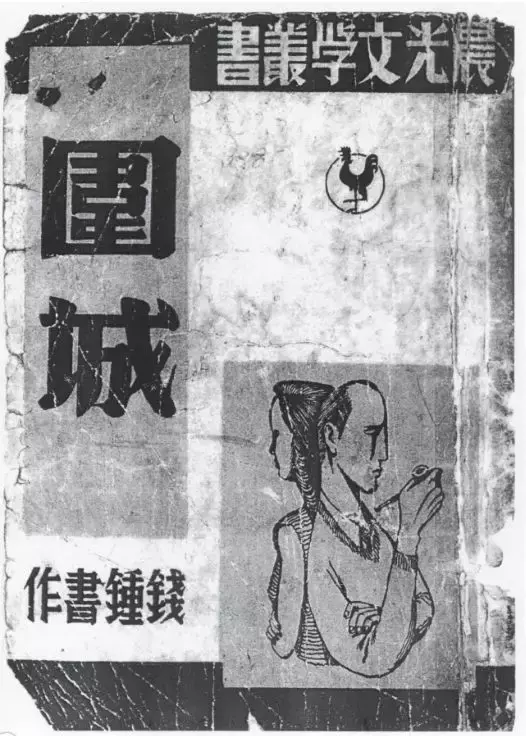
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《围城》
“我见到她之前,从未想到要结婚;我娶了她几十年,从未后悔娶她;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杨绛在书上读到这话,读给钱锺书听,钱锺书说“我和他一样”,杨绛说,“我也一样”。
因为足够优秀,我不必卯着劲儿证明自己。
因为喜欢看你比我更优秀,一切牺牲我都甘之如饴。
所谓人间佳话,不过如此。
5
杨绛先生的晚年,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打击。
先是女儿钱媛过世,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,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完全体会。
之后是钱锺书撒手人寰。

从前的“我们仨”,终于只剩下她一个,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。
但是在字里行间,她依然极其克制,仿佛竭尽全力要把那巨大的悲痛吞咽下去。
回忆从前的三口之家,她写:
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“我们家”的寓所,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,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
想念携手一生的伴侣,她写:
我曾做过一个小梦,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。他现在故意慢慢走,让我一程一程送,尽量多聚聚,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。这我愿意。送一程,说一声再见,又能见到一面。离别拉得长,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?我算不清。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,愈怕从此不见。
实在难以克制的时候,她的文字仿佛都在颤抖:
我使劲咽住,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,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……
如今,先生终于不必“使劲咽住”这满腔热泪。

“剩我一个了!”
2003年岁尾摄于北京三里河寓所
世界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。我们不知她最终找到了怎样的归途,但在这冷漠、纷扰、诡诈、满是裂痕的人世间,我们感谢曾经拥有过这样努力不负天赋、舍己不负爱情的灵魂。